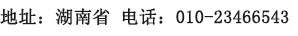文/陈乔文
全文共字
01
今天农历六月十一,是港湾逢集的日子。
街上行人如织。宽阔的街道两边被流动摊贩把持得水泄不通。电喇叭的叫卖声此起彼落,蛊惑着行人的双耳,甚至卖老鼠药的广告词经过一番修饰也变成悦耳动听的语言。
晨阳斜照过来,各种各样的服装和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把金色的水泥地装扮得五彩缤纷。那些平时固定在港湾街上的肉案、菜摊、日杂百货店也把鲜肉、蔬菜、百货移到路边,一扫往常慵懒的倦容,鼓起腮帮子精神抖擞地吆喝起来。
田家小吃店这个时候也是最忙碌的时候。
“这碗面条送到西边卖服装的陶老板那里。”
“这碗面条送到东面卖水果的张老大那里。”
“这碗面条送到对面卖瓜子的小孙那里。”
……
田嫂用伶俐的口齿吩附着田哥,把一碗碗面条送到指定的摊位。怕路上有灰尘落入碗中,碗上还要罩上一个盘子。再加上街上行人很多,怕碰了撞了,田哥用左手托住碗底,右手张开五指捂着上面的盘子小心翼翼地走着,样子歪歪斜斜有些畏葸。退休干部周胖子笑着对他说着那句政治台词:“胆子放大一点,步子迈快一些。”他便调了调步子,挺了挺胸脯。可没走几步又故态复萌。
整个上午田哥来往于店面与摊位不知多少个来回。送面条,取碗,收钱。用他自己说的一句话,“脚都走出老茧了”。越来越高的气温使他气喘吁吁,在太阳的反射下,满脸泛着金色的光芒。
不大的小吃店里被人塞得满满当当,田嫂在厨房里紧张地忙碌着。一碗碗肉丝面、青菜面、鸡蛋面被她满面春风地端到桌上,又忙着撤下前客留下的残羮剩汤。短短的身段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就这样还是有人不停地叫。
“哎!老板娘,来碗肉丝面加鸡蛋。”
“哎!老板娘,剁半斤老鹅。”
“老板,把桌子收拾一下。”
每当遇到生意火爆的时候,田哥就会头皮发炸。混乱无序的场面使一向慢条斯理的他无所适从,一股无名的恼火从胸腔转化到胳膊上,阴着脸咬着牙把手中捧着的一摞待洗的脏碗,直着身子扔进浮着白色泡沫的洗碗盆里,伴着一阵清脆的瓷片碎裂声,八只碗碎了四只。
邻居王老师捧着茶杯,踱着方步过来看了下不紧不慢地说:“下次碗儿要换铁的。”
开粮油店的李二娘子笑逐颜开:“岁岁(碎碎)平安,事事(四四)如意。”
随着喧嚣的集市在午后都收了摊,田哥的小吃店变得空旷了许多。田嫂用一个大的盆子洗海带,做着明天卤菜的底工,田哥趁着机会在躺椅上补觉,不一会儿就打起了鼾声。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在门口细声叫道:“剁点猪头肉。”田嫂腾不出手来,对躺椅上的田哥说:“哎!有人剁猪头肉。”
声,纹丝不动,鼾声依旧。
第二声,纹丝不动,鼾声停止。
第三声嗓门响亮,田哥从躺椅上站了起来,腮帮子上的印纹印证了睡眠的深度。他用手抹了下满是不快的脸,惺忪的眼睛乜斜着小姑娘问:“剁多少?”
小姑娘怯怯地说:“剁十块钱的。”
田哥眼睛一愣,话中带刺:“我还以为你要做多大的生意呢。”说罢,气哼哼地打开橱窗,拎出一小块满面红光的猪头肉,“叭”地扔到电子秤上,然后按了几下阿拉伯数字说:“十块二角,算十块钱。”拿到砧板上“咚咚”地剁着,刀上带着杀气,砧板剁得上下弹跳,桌子也跟着颤抖。
小姑娘丢下十块钱,逃似的离开了。买猪头肉买出虎口拔牙的感觉。
02
田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恼火着呢。
田哥的恼火是有由来的。每晚十一点才睡,早上三点又起床。这种早起晚睡的日子简直是在受刑。他是多么怀念两年前的日子啊!
田哥家在两年之前家里还是专门卖卤菜的,生意还说得过去,但占着夫妻两个劳力有些富余,也是田嫂指点他在机械厂谋得一份保安的差事。机械厂离家说远不远,说近不近,骑电动车大概十几分钟的光景。工资虽然低点,但工作十分安逸,一天八小时,一年四季呆在四面墨色玻璃的保安室里,夏天吹冷风,冬天吹暖风, 的工作量就是每天揿几次电动伸缩门按钮。另外还免费供应三餐,顿顿有荤有素。没几个月,身体宽了,肚子圆了。一套灰色的保安服,愣是被穿出将军的风度。一副满足的笑容均匀地布满脸上。他常自语:“神仙的日子也莫不过如此吧。”
因此,田哥在上下班的路上,常常快乐地哼着自编的顺口溜:
老汉今年五十三
机械厂里做保安
工资两千一百三
另外免费吃三餐
下班以后奔港湾
……
这样安逸舒服的日子在两年后戛然而止。田家大姐和大姐夫因为上了年纪的原因,要把经营了几十年口碑很好的小面馆关了。头脑活络的田嫂有心接盘,田哥却像是被电击一样弹跳了起来,指着田嫂说:“你就像你老子。”
田嫂的确像她老子有经济头脑。田嫂的父亲养鸡,办厂,种花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造了楼。县里把他当作致富楷模,把他的致富经验在全县推广,上过电视登过报,县里乡里作报告。
田嫂从小耳濡目染,大家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时,她和田哥早已洗净了腿上的泥星子,在港湾街上开起了卤菜店。
田哥有自己的想法,大半截身子快入土的人了还那么折腾个啥,人来到世上不就想过个安逸的日子,难道是来找罪受?找苦吃?找神烦?
田嫂铁了心要把小面店盘过来,天天逼着田哥打辞职报告。弄得二哥上班常常走神,居然两次老总的车被拦在外面,被队长臭熊了一顿。他苦苦思索了半个月,终于想出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方法。他对田嫂说:“我继续上班,你雇个帮手,用我的工资开帮手的工资。”
田嫂坚决不同意:“夫妻店,夫妻店,请来的人做事能有自家人上心?”田哥嗫嚅道:“你以为我做事就比请来的人上心?”
田嫂一向在家占主导地位,尽管田哥还作苦苦挣扎。但胳膊再粗,能粗过大腿?
在田家大姐和大姐夫的倾囊相授下,田家的小吃店开业了。店还是原来的卤菜店,只不过添了几张桌子,几张凳子。没有鞭炮,没有花篮,甚至没有店名,只是田哥没精打采地在左右两扇玻璃门上分别贴上“卤菜、面条”四个猩红大字。
在离职那天,田哥与其说向同事们告别,不如说在向他安逸舒适的日子告别,他看着日日相伴的保安室以及里面熟稔的每一件物件,抚抚这件,摸摸那件,睹物思情。不敢想象今后的日子,匆匆跨上电动车,不然恐怕要洒泪了。
从此,田哥看山山不青了,看水水不亮了。一天到晚心里灰蒙蒙的,再也听不到那抑扬顿挫的顺口溜了。
03
生意闲暇的时候,田嫂总会把桌凳擦擦,地面拖拖,偶尔目光会触碰到墙上的一张喜报。田嫂斗大字不识两箩,不知道喜报上写的什么,只知道是儿子在部队立了个三等功。上面发了这么一张纸,叫贴在墙上。这张纸虽然不太醒目,但来吃面条买卤菜的人看到都要夸奖一番,田嫂觉得脸上很有光。
记得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来了两个自称武装部的同志来到田家小吃店,证实了田哥以及他儿子的名字后,转身在门外“噼噼啪啪”放了一阵子鞭炮,弄得大家都莫名其妙,引来很多人来看热闹。
武装部的同志进了门,用标准的姿势和热情摇撼着田哥的双手连声说:“恭喜,恭喜,祝贺田志刚同志在部队荣立了三等功。”还说了些同勉的话。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尺许见方像奖状一样的一张纸,说这是喜报。田哥田嫂一脸懵懂,不知三等功是啥。武装部的同志又从包里掏出一沓钱说是奖励,田哥田嫂两双眼睛四束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钱上,才明白三等功原来是一沓钱。田哥高兴地涨红了脸,搓着双手在屋里打转。田嫂激动得脑子一片空白,眼前扑朔迷离变得不真切起来,只看到武装部的同志嘴一张一阖,根本没听进他们说什么。
当田哥笑眯眯地用双手接过钱时,田嫂便觉得那张纸已经显得多余,折折叠叠准备扔进垃圾桶时,被武装部的同志拦住了,说:“刚才不是对你们说了嘛,这张喜报应该贴在墙上, 装裱起来,是你家儿子的荣誉,是为你们脸上贴金的。”
看到喜报,田嫂自然会想起儿子,想起儿子自然会想起孙女。她掏出手机翻开孙女的照片和视频,看着千里之外的孙女像一只小天使又跳又唱,稚声稚气的童音使她有了掐着肝肠的亲和疼,脸上溢满了儿孙绕膝的幸福笑容。她把相册里所有孙女的照片和视频反反复复地看,也反反复复地笑。笑够了,笑累了,便有了与儿子打电话的冲动。随着“嘟——嘟——”的声音越来越久,她脸上失望的颜色越来越重,直至话筒传来:“你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她叹息一声:“念书念到牛屄里了。”心暗下许多。
田哥田嫂就一个儿子,念了小学念初中,念了初中念高中,念了高中念大学直至到部队。书是越念越多,与他们感情却越念越淡。除了要钱几乎不主动往家打电话。田哥田嫂打电话过去十次有八次不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