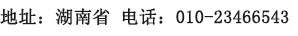「我几日来都摸不到秦不言的影,说是闭门谢客,但别人能访得,唯我访不得。」朱清说。
「他不见疯子,」我对朱清说,「他觉得你在发疯呢。」
朱清不置意见。
见九妩肯开口,我便问:「如果那蛊术成了,除了达到他的目的以外,究竟还会怎样?」
九妩一字一字道:「让我索走一点点寿命呗,就一点点。」
当归这时把我拉出去,道:「她没有说谎。」
「九妩为何怕你?」
当归微笑道:「我怎么不这样觉得?不过,我可能真是凶了点,是不是吓着你了?」
算了,谁从前没走过几个地方,打上几场架。
我悄声说:「论凶,你不及鄞王半分。」
「还有你们口里的那个国师。」
「嘘。」
「九妩无法可施的话,你那个鄞王会有可能死掉的,」当归生硬地安慰我,「你不要伤心太久,人会蔫掉的。」
我怔了怔,这话虽不太好听,可也生不出气来。
屋里突然传来九妩高昂的声音:「七月,你总会吃苦头的。」
「七月?你从前的名号是七月?」我问当归。
「不太记得了,是这个吧。」
「我倒觉得好听。」我随口道。
当归突然又扯住我,神色有些不自然,道:「你想知道九妩为什么听我的话是吧?」
「你说我就听。」
「我刚变成人形的时候,是九妩的师父给了我衣裳穿,后来还给了几口饭吃,我就帮着在他那里做些洒扫的杂活,毕竟也没什么地方可去的。我在那里待了许久,师父才把九妩带回来的,九妩以为我是她的师兄,可我从来没有在她师父身上学过一点点的巫蛊术,所以就只是个杂役,可她师父对我是不错的,甚至还劝过我跟着他学些皮毛,说是肯定有用处。我不信,于是就什么都没学。九妩性子傲,总来缠着我说要切磋,否则师父会不满意,我说要切磋扫地还差不多,那些个什么咒法我是一概不通,她觉得我看不起她才这样说,所以就用了手段逼我。」当归细细道来。
我不禁猜道:「她对你下蛊了?」
当归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说:「是情蛊。」
我懂,我听懂了,心里雀跃着八卦的意味,问道:「你中了吗?中之后是怎样的?」
「我没有中。」当归说。
「啊?可九妩说她从未失败过啊」
当归笑着说:「这蛊她是给我下了,可没下成,因为对我没用。九妩的师父说,是因为我天生就少一瓣心,那些沾染了情啊爱啊的蛊术,都拿我没办法。」
「她给你下别的蛊了?」
当归轻飘飘说:「没有,之后我就把她给绑了,绑着扔到后山去,让她听着狼叫过了一夜,她就再不敢对我下手了。」
「你真敢做呀?」
当归:「我为何不敢?我也懒得管她死活,死了我就去收尸,活着我就去松绑把人给放了。」
「九妩师父也任你罚她?」
「九妩不敢说实话,这事只能被掩过去。」
我仍是很好奇:「你还是没说中了会怎样呢,你也不知道吗?」
「我听九妩师父提过,他的原话是求爱而不得能噬咬人心,最后活活把人逼疯。」
我愣了愣,道:「我错了,我不该先觉得你狠心的。」
「九妩本意不是让我发疯,是要逼我解蛊,可惜我不吃这一套,还险些把她的性命给折腾没了。」
见我不说话,当归垂眸问道:「我是不是又做错了?」
「没有,我也不会把你关笼子里面的。」
当归笑了笑:「好。」
我又问:「九妩解决不了的事,她师父能解决吗?」
「来得及吗?西南边陲离这里很远很远。」
来不及。
当归已然这样说,我只能再去找人,国师秦不言不肯露面,便去找妙法。
妙法原先也不乐意见我,是我夸大其词说尹亭要断气了才肯出面,然而他也只是来看了尹亭一眼,留下一句死不了,立刻就走。
「你不管他了吗?」
「没什么可管的。」
「你是在介怀上次的冲撞吗?我能道歉的。」我对妙法说。
「既说了死不了,你就不必再来纠缠。」
死不了,可是也醒不来,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我头都大了。
尤其是不知谁在兴风作浪,短短两日就能把鄞王性命垂危这一件听着就假的事传得满京都是。
于是我一回府,就听见小厮禀报说客人来了。
还来了不止一个。
全都是贵眷。她们叽叽喳喳的一通说,意思都一样,让我节哀。
「颜妹妹,你也别太难过了,鄞王吉人自有天相,定能撑得过去的。」
「即便撑不过去,侧妃你还年轻,又有难得的美貌,他日再嫁也是不愁的。」
「我家老爷一向最是敬佩王爷的了,如今突闻噩耗,可是愁眉不展呢。」
「究竟是那样阴毒啊?好端端的一个人竟要这样没了。」
……
我觉得尹亭如果真的没了,是被咒没的。
我不懂得人情往来,只觉得这提前备好的哀悼让人烦闷不已。
尹亭教过我许多,唯独没教过我要如何应对这种情形。
我忍耐不了,起身往外走。
突然间撞上了前面的身躯,让我眼前直冒星。
一只手环上我的腰肢,将我扶稳,「腿伤未愈,还走那么快?」
这把声音夹杂着罕见的无奈,宠溺和温柔。
我抬起头,瞳孔微增。
场上忽然变得躁动起来,响起繁乱的,被压低的细碎的交谈声。
我提声对尹亭说:「我头疼,赶着回去躺着。」
接着,又用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说:「你快点。」
你快点处理,然后快些回来见我。
那一厅的人,都是尹亭去打发。
人还没见回来,我就听到了远远传来的咳嗽声。
看见尹亭的身影时,我迎上去,揽着他问:「都走了?」
「她们见是我来,都走了。」
「她们料不到你会醒,我也料不到,因为连九妩她都说无能为力。」
尹亭:「我自己醒过来的。」
「你醒过来怎么比睡着还吓人?脸上一点血色都没人,像鬼。」
「是吗?可我还不舍得当鬼。」
「你既醒了,就不会再晕死过去吧?」
尹亭:「不会了。」
我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你不要再找九妩了。」
「你当时以为我们有染时,可都没说这话呢。」
「有染就有染,起码不是下蛊这么吓人的事。」
尹亭微微叹了口气。
「你没答应我,我说让你别找九妩了。」
尹亭偏偏不肯允我这一点:「只是受些小罪,死不了的。」
「小罪吗?只是停下来就要昏死过去,那万一出了别的岔子呢?」
尹亭轻轻抱我,揉着我的脑袋说:「不会,我怎样都能挣扎着起来,我有舍不下的东西。」
我口舌不够灵敏,支吾着说不出别的话来。
尹亭喝了碗药,带着我进宫了。
他们父子见面时,我低着头绞手帕。
手帕快绞出丝来时,我听见尹亭同皇上说:「儿臣醒来就听身边的人说,是侧妃四处去托人寻药,后来又亲自试药,才保了儿臣一命。」
啊?没有吧?听谁说的?
我尽量低下头,不使疑惑露出来。
尹亭继续道:「父皇,儿臣求个恩典,赐颜氏正妃的位子吧,毕竟入府以来都是她在理事。」
我好像也没有干过这个。因为我不会算账,也不懂得御下,我似乎没什么用处。
「你当真这么喜欢?」皇上缓缓地问。
尹亭的话很出乎意料,然而皇上平和的反应更是让我惊讶,隐约记得前两日他还抱着要为尹亭觅高门贵女的心思。
不会是那术法……还在吧?
尹亭道:「是,儿臣很想扶颜氏为正室。」
皇上挥了挥手:「你且先回去歇息,毕竟无论朕给的是什么答复,你都难免要费心力一场,你这身子耗不起,晚些再说。」
「来时见到宫外的芍药开了,儿臣觉得移些到宫里来,定是好看的。」尹亭突然说。
皇上似乎想到了桐花巷门前那一盆,怔了一会,慢慢点头道:「听你的。」
尹亭颔首告退。
在还没完全离殿时,我听到皇上在身后幽声道:「你真是越发像你母妃了,心思深,偏偏身子又不好,于是来回地折磨自己。」
尹亭的步伐没有停下,全然当没听到。
我觉得,所有人包括小炎丈夫口里的她,都不太像我认识的小炎。
朱清说得对,小炎爱尹亭的父皇,所以甘愿磨损本性,也要留在他身边。
「祈儿,你听清我父皇的话了吗?」尹亭突然问。
「听清了。」
「你说他今晚还去不去桐花巷?」
「他现在想念闫妃,所以大概是会去的吧。」
尹亭淡声道:「真替我母妃难过啊。」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提什么移宫外的芍药花进来?这不是引他思念吗?」
「是劝他把那位接进宫里,遮遮掩掩的,显得是我亏欠下来似的。」
我正欲回应,却看见三公主携着两岁的小郡主款款而来,于是噤了声。
尹亭的这个三姐姐我只见过一次,自然是无话可说的。而且瞧尹亭的表现,他和三公主应该也不太熟络。只是,尹亭似乎很喜欢小郡主。
他蹲下来和小郡主说话,还会逗她笑。
三公主见状,笑道:「七弟既然这么喜欢我们郡主,不如抓紧些和侧妃生上几个吧。」
尹亭亦笑,说好。
我想起尹亭在暗室时同我说,等蛊术成功,我们还能生个孩子。
原来他是喜欢孩子的,平日里一点都看不出来,倒是很像随时很把娃娃吓得嗷嗷哭的行事作风。
我觉得生条小蛇也不错,可是依尹亭的身份来看注定是要把这苗头给掐灭了的。
「好了,我们进去吧。」三公主把郡主抱了起来。
等三公主一走,尹亭又低低地咳了几声。
宫里耳目多,上了马车我才敢问:「怎么醒了还不算好?真要病一场了吗?」
「你坐过来些。」
我以为他要解释,于是凑过去,不料肩上突然重了重,然后听到:「给我靠靠。」
「给你。」尹亭顺势塞了一粒小物件到我手里。
我仔细一看,是郡主刚才送给尹亭的糖。
我吃起糖来,口里甜巴巴的。只是我忍不住像个刺头一样说话:「我不想当那什么太子妃。」
尹亭直起身来看着我,缓声问:「为何?」
「不好玩,不喜欢。其实同什么正妃不正妃的没关系,我也是两三年前才知道还有这样一回事的。」
「怎么就不喜欢了?」
「我不会御下,不会管事,连规矩都只会像请安和下跪这样的,现在的皇后就是当时的太子妃吧,可我一点都不像她,更比不上她分毫。」
尹亭笑:「你不懂事,我不识相,般配。」
我怔了怔,困惑快要溢出来。
尹亭敛回笑意,问:「你还觉得皇宫里很闷是吧?」
「没有比那里更闷的去处了。」
尹亭想了想,说:「国师这两日要南下,是为公事,可我同你也并非不能去。」
「途经姑苏吗?」
「经的,或者经那里之后直接停下来。」
我一开始觉得高兴,可反应过来后又隐隐觉得不对劲:「可是……我说的不是要南下,我说的是不要……」
当我看清尹亭冷清的眼神时,我顿时打住后半截。
我忘了,他如今是身子不好,可脾气还是那样。
「祈儿,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度。」
我轻轻点头:「知道了。」
尹亭说了要南下,第二日就带我启程。
在途中时,他问:「你是何时同我母妃在一起生活的?」
「就是在姑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住了好久。」
「然后呢?」
我扁了扁嘴,说:「然后她就嫁给了你父皇啊。」
尹亭问:「她嫁给我父皇之前,是什么样的?」
「爱笑,天真,」我顿了顿,「和我在京城里见到的人都不一样。」
「也和我知道的母妃不一样。」
我恹恹地说:「个个都说她郁郁不快,我快难过死了。」
尹亭垂眸,若有所思道:「都会这样吗?」
「什么?」
尹亭掀开帘子,轻声道:「没什么,你看看外面,太阳西沉了。」
我瞄出去,第一反应是道:「咸蛋黄。」
尹亭看着我笑。
虽然是突然敲定的行程,然而尹亭的踪迹始终很招眼。好几次,我在里头不见刀剑,但总有厮杀声传进来,偶尔把我从梦中吵醒。尹亭在时,会捂着我的耳朵,不在时我就自己缩着。
有一次尹亭在我身边时,隔着手同我说:「熟人来了。」
「什么意思?」
那些刺耳的声音消失时,尹亭带我出去,一眼就看见了国师秦不言。
「殿下带这么少人?」秦不言笑着问。
尹亭:「想着你在,干脆减了人。」
秦不言:「多谢殿下信任。」
我们一起吃饭时,尹亭会提一句带我去姑苏看看。
秦不言还会作出一副惊讶的模样:「侧妃原来是那里来的。」
真是……好会装啊。
走了将近一个月,尹亭几乎日日都能收到从京城传过来的信,我起先会凑过去看,只是看不懂,后来就不爱瞄了,直到我看见他在展开一封信时,还特意转过身去看。
我去扒拉时,尹亭偏偏不让我看,还要把纸张揉成一团,道:「你求求我啊。」
「我不干,你不会又联系九妩了吧?」
「你提醒我了,我险些忘了还有正事。」
我蹙眉,继续去抢,尹亭手劲一松,纸团落了地,滚出去,到门槛处才被拦住。
恰好有一只鞋履悬在纸团上。
秦不言收回脚,弯腰捡起纸团,慢慢展开,看完后没有说什么。
我开口问:「说了什么?」
秦不言看了一眼尹亭才开口回答:「朱清卸任离京了,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个小公子在身旁陪侍。」
那就是当归。
「是有多迫不及待。」秦不言幽声道。
「他心思看着就不像是在官场上的,」尹亭随口道,「当初科考的时候也不知是不是走错场子了。」
我瞥了瞥秦不言的脸色,还笑了一声
秦不言懒得理我,只同尹亭说:「殿下,外头有人要求见你,臣觉得可以见一见。」
尹亭起身:「那就去见。」
他方走出几步,突然停下停,咯出血丝来。
我惊了惊,递上手帕。
秦不言亦有些无措:「殿下这是……怎么了?」
「咳多了伤喉咙,」尹亭摆摆手,「无妨,我顺便去让大夫看看。」
我跟着出去,却被秦不言悄无声息地拦下了。
等尹亭的身影已然不见,秦不言才道:「有事问你。」
我的心提了提,生怕是他看出来什么了。
尹亭这段时日身子虚弱,容易遮掩不住某些气息,所以让朱清看出来,而今秦不言会不会也……虽然我总是把尹亭黏得紧,好让自己的气息盖过他的,但也不知道秦不言究竟有无那个能耐。
「你不觉得鄞王身上有些不大对劲的东西吗?」
果真……
我摇摇头:「没有啊,你觉得有什么?不会是他中邪了吧?」
「还真说不定是中邪了。」
「可我日日同他一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啊。」
「那是你蠢。」
「我不是,」我提步就走,但突然想到秦不言或许会查下去,只能回头说:「他找了个蛊师回来。」
「那个被带进府的不是侍妾。」
「不是。」
「给谁下蛊。」
我脸不红心不跳道:「给我。」
「为何要给你下蛊?」
「他一心想给我换个堂正地活在人族里面的身份,你明白的。」
秦不言:「邪术一桩,但还真有些可行性。」
「你当初想要我生个嫡世子,不也是想这样做吗?」
「的确,」秦不言说,「你不是不乐意吗?倒肯了?不会真的贪上了那至贵之地的荣华吧?」
「没有,我把这事搅黄了。」
「没意思,」秦不言顿了顿,回过神来,「给你用蛊,关鄞王什么事?」
「蛊师要索他的命呗。」
秦不言冷笑:「难怪你要搅了这事。」
我一心虚就会张牙舞爪:「大人早该想明白了,枉素日里谁的心思也比不上你活络。」
「颜祈。」
我听出警告的意味时,连忙快快走去,然而还不忘留下一句:「我是有靠山的。」
秦不言大抵真的被气到了,一日两餐都不肯从房里出来同我们一起吃,尹亭还随口问了句:「国师这是在斋戒?」
「我瞧他脾气古怪,还真说不准是为何。」
尹亭悠声道:「你又不与他相熟,倒是很振振有词。」
我抬头看窗,顾左右而言他:「晚上是不走夜路的了,那就是还得在栈子里留一晚,那我们去镇上走走?」
「依你。」
经过一番磨练,我已经能像叙家常话一样指着镇上过往的人群对尹亭说道:「你猜猜这里面谁是为你来的刺客?」
尹亭想了想,向着西边方向的一个卖花翁抬了抬下巴:「这个,隐于市集,最方便隐藏不过了。」
「我不信。」
我走过去买花,尹亭与我并肩走,双手交束在身前,手心握着,似乎在攥着什么。
我随手指了一束,在卖花翁递给我手中的下一刻后,尹亭展开手心,露出几枚铜币。
原来拿的是钱,我还以为有小刀呢。
我拿着花走开,小声嘟囔:「你说错了,这个不是。」
「哄你过去买花罢了,还真信。」
「你……」我滞了滞,察觉到有人弄痛了我的手臂。
一回头,对上一张傀儡面具。
我吓得往尹亭身后钻过去,与此同时,一把银刃悬在面具前方,眼看着只要尹亭稍用些力,面具人的眼睛可就保不住了。
「是他,是他掐了我。」我指着傀儡面具说。
然而我看见尹亭慢慢放下银刃,不解道:「我指错了人吗?」
「你没指错,」尹亭道,「但你不妨认真地看看是谁。」
傀儡面具被对面人摘下,露出一张玉面。
「朱清!是你。」我又惊又喜。
「凶巴巴的,你可比我这面具吓人。」朱清嗔我。
「是你要戴着这面具的,我认不出可太正常了,好端端的你不会是进傀儡班子了吧?」
朱清:「这路上戴着的又不止我一个,取乐罢了。」
「你比我们晚出京,怎么也到这里了?」
朱清:「有时会不好好走路,不好好坐车,就快了些。」
「当归呢?」我问。
「买糖去了吧,我给他银子了,」朱清看向尹亭,问道,「看我这妹妹这模样,数日来是见了不少血?」
尹亭:「她没亲眼见着那些场面,只是心里知道有这么回事,不算吓得厉害,只是多思多虑了些。」
朱清:「我听说国师也南下,你们是一道?」
尹亭:「算是。」
朱清:「那我和当归另行安置。」
尹亭:「你得罪他了?」
朱清:「实话说,秦大人倚重我,我先斩后奏就把辞呈给交了上去,他应是对我很难心平气和的。」
我小声道:「全对。」
话音一落,另一张傀儡面具亦入了视线。
这次我能认出来了,绝对是当归。
手上还拿着三根糖葫芦。不对,为什么只有三根,现在有四个人啊。
那人摘下面具的那一刻,我有些意外。
不是当归,是跟在秦不言身边的一个侍卫,身和当归有些像。
朱清皱了皱眉,向侍卫问道:「我身边的那个小公子呢?」
侍卫回话:「朱大人,那个小公子被我们主君请了回去,另外,也想请你去一趟。」
朱清闻言,拔腿就走。
侍卫把三根糖葫芦递给我,我懵然地尽数接过来,呆呆地看着朱清跟着侍卫走。
「这是在干什么?」我问尹亭。
尹亭:「秦不言觉得这样做朱清就会过去。」
「他不会杀了朱清吧?」
尹亭:「杀他有什么用?」
「我现在就得回去看看,起码你在,国师不敢对朱清怎样。」
「又是我当令箭?」
我抽出一个糖葫芦:「请你吃。」
尹亭低首,微微张口
我快速地递上去让他咬了一口,还小声地问他:「被你的暗卫看见,会不会折了你的威严啊?」
尹亭不紧不慢地吃完一粒,才道:「他们见过的事,何止这桩?」
「比如?」
「我在街上咬你啊。」
「丢死人了那会。」
「你不回去看看你的好哥哥了?」尹亭问。
我一跺脚,「你早该说。」
匆匆回到客栈时,一楼的厅堂不知是被清过场子还是夜里人都回去歇息了,一共就只见两个人。
朱清坐在秦不言的左侧,微微低着头。
而秦不言正在慢条斯理地……吃糖葫芦。
只吃剩一颗了。
这个场景如果换个人来做都会是一副轻松柔和的景象,偏偏是秦不言。怎么说呢……我瞧着觉得他不像是在咬山楂,更像是在啃朱清的头颅。
秦不言吃完最后一颗山楂时,抬头就看见了我和尹亭。
他笑道:「王爷,侧妃,天色尚早,怎么回这么早?」
我说:「没有伴,不好玩。」
秦不言指了指上面:「那个叫当归,在楼上呢,侧妃嫌闷的话,可以找他说说话。」
尹亭拍了拍我,道:「你上去,我留在这里。」
我路过秦不言身边时,特意停下来问:「怎么让朱清干看着?也不请他喝杯茶。」
「这里的茶太糙,配不上朱大人。」秦不言说。
「祈儿,上去。」尹亭在身后出声道。
我一步三回头,发现尹亭都是在看着我,我只好使了使眼色,让他记得要施些威严,镇一镇秦不言。
我上楼去,却忘了问当归是在哪个房间,又不好去逐间看,只好先回自个的屋子,一推门,满脸惆怅的当归同我四目相对。
「那个秦大人的侍卫把你带回来的时候,可有动粗?」
当归摇摇头:「没有,他们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跟着走了。」
「可你看起来很不高兴。」
当归平静地申诉:「我总共就匀下一根糖葫芦,那个秦大人二话不说就拿了去,不容我分辨,竟那样夺走了,流氓一个。」
「他平日里做派就这样,咱不好跟他计较。」
「我知道,我怕惹事,就什么也没说。」
我又问:「朱清说要带你去哪?」
「姑苏,他说那里清静。」
「我这一趟也回去。」
当归扬了扬嘴角,笑道:「那我们始终是在一块的。」
「我可能呆一阵就要走,不过只要你们在那里,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去都能找得着人。」
当归正欲开口,在听到突如其来的推门声后,从窗子跳了出去。
这可是二楼……我扒着窗框,看到落地的是一团白绒绒才松了一口气。
进来的是尹亭,他微微疑惑了一下:「你扔下去的?」
「我残害同类做什么?明摆着是你们一个个吓着他了。」
「好,这锅我背就是了。」
我点点头,表示认可。「我哥哥呢?国师有没有把他怎样?」
「只问了朱清几句话,言语不过分,朱清答了也就当做过去了。」
「没骂人?」
「我在时是没有的。」
我想了想,问:「那朱清到哪安置去了?」
「这里起,左边的第三间。」
我又扒在窗框上,这里正好对着院子,有谁进出能看得一览无遗。趴着好久,都没看见朱清离开,看来是真被留下了。
尹亭的手环到我腰间上时,我觉得身上一重。
他知晓我在看什么,轻声问:「既然此行目的一样,你不会到最后不舍得走了吧?」
我老实道:「不舍得,一定不舍得。」
「颜祈。」
「你又不喜欢我编谎骗你,我只能这样说。」
尹亭掐着我的腰说:「我有时喜欢你骗我,骗人的话好听。」
「不说,睡觉。」
我刚躺下来又立刻扒着尹亭问:「国师不会半夜起来让人暗杀了我哥哥吧?」
「他是嫌生活烦闷,特意染桩杀孽来逗趣吗?」
「万一呢?」
「秦不言倒不至于那么阴险。」
「我觉得难说。」
尹亭:「你总不会比我更了解他。」
我其实……挺了解秦不言的。我刹住车,害怕一着急把什么都招呼出来了。
一觉到天明。我立刻去检查是否有命案。
都还活着。
倒是一早就起来的秦不言见状把我给白了一眼。
「你不上朝,怎么还起那么早?」
秦不言:「那串东西,甜得发腻。」
「你得赔给当归一串,否则人家也太冤了。」
秦不言带着挑衅的意味道:「我偏不。」
……一大早的我又被气到了。
私怨归私怨,在南下的路上还得装着和和气气的,否则尹亭会觉得奇怪。
幸好到姑苏时,只我们夫妇和当归朱清他们停留下来,秦不言得去忙他的公事。
朱清是一早就做好准备的,一下马车,眼前便是一间干净宽阔的宅子,周边环境还十分安静清幽。
别家大人致仕之后才有的清静他倒是早早就有了。
我有那么一刻觉得尹亭或许也会有那么一些翘首的。
我在猜尹亭的心思,没想到尹亭也在端详我的神色,问:「你眼睛都直了,有这么喜欢吗?」
「喜欢,喜欢得不得了。」
「好办。」
我看向尹亭:「你又寻思着在哪建?」
「路上慢慢想。」尹亭跟着朱清进去。
看,他先走,肯定喜欢这里。
之前在京城练了许久的长寿面,当归终于能拿到朱清的案前,只是看朱清的神色,那依旧很难吃。朱清本就属于遇事不动声色的性子,只是都还不能藏住那微弱的嫌弃。
难怪当归说从前在九妩师父那里做的都是洒扫那样的杂活,看来是没碰过能入口的东西。
锅里还剩一点,我端给尹亭了。
只是……他怎么没反应啊?
端着那副斯文矜贵的作派,不动声色地吃完了整碗面。
我们在宫宴上时,尹亭可是连御膳都能挑剔上几分的。
所以我从锅里捞这些余下的时候,纯属是要逗他罢了。
「不难吃吗?」我忍不住问出口来。
尹亭放下银筷,微微困惑地看着我。
我指了指面碗:「这个,是当归做的,可他进膳房就是去受磨难的,简而言之,我和朱清都觉得不好吃。」
尹亭怔了怔,慢慢地用绢子拭了拭嘴角,道:「是咸了。」
可当归忘了放盐。
我愣愣地问:「你是不是味觉出了什么事啊?」
「没有,没什么事。」
「如果我有心要试,很容易试出来的。」
尹亭这才说:「舌头是不太灵了,却也不碍事。」
他说的是损了五分,那实际上便是损了十分。
竟真的吃不出味道了。数日前的那串冰糖葫芦,我一颗颗塞给他的糖葫芦,原来是半点甜味都尝不出来的。
「什么时候的事?」
尹亭:「今天。」
「问你还不如我自个猜。」
尹亭:「你猜猜看。」
「蛊术失败之后,是吧?」
「或许是咳得厉害才没的,日日都咳,吃什么都没味道。」
「那上街抓药去,哪有顽固的咳疾,无非是药还不够苦。」
尹亭:「你如今说话怎么一套套的?」
「朱清从前就是这样给我治病的,」我想了想,说,「光吃药不够,你把九妩的师父请过来吧。」
「那人要是能来,我何必要同九妩周旋?」
好像也是。
「那你别管我。」
我匆匆地去买药回来,在等小厮煎药时,我在院子里瞎逛,逛着逛着,又发现了一个笼子。
朱清是有些管教人的魄力的。
我好奇里头究竟有多大,自己钻了进去,合上笼子的那一刻透过缝隙与出来寻人的尹亭四目相对。
我化作一滩毛团才能稍微化解一下尴尬。
尹亭一步步地往笼子走过来,细细端详着,也许也有在笑,只是我闭着眼没看到。
笼子被打开时,我被他抱出来。
就这样吧。
尹亭带着我一路穿过庭院,我慢慢睁开眼,看见朱清和当归又在玩牌。想想当归脾气算是好的,这么大一个笼子哐的一下落到眼前,他还能心平气和地与买笼回来搁置的那个人对牌。
我摇了摇尾巴。
尹亭便转了方向,往那二人走去。
朱清先是不经意地往这边看了一眼,然后移开目光,片瞬后又看过来,接着收回视线,几番来回,他终于确定尹亭怀里的是我。
「她怎么了?」朱清问。
尹亭道:「返璞归真。」
朱清:「我记得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
「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朱清:「您说得对。」
尹亭坐下来,安静地看朱清和当归打擂台战,可他的手也没闲着,一直在摸我的头。
我睡过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发现尹亭在喝药。
「怎么样?这药苦不苦?」
「苦。」
「胡说,这剂是我让人去煎的,不会苦的。」
尹亭却咬定是苦的。
我叹了口气。果然是没好。
朱清知道尹亭在吃食上挑剔,还特意来问我他的口味,我想了许久,最后憋出来一句:「要颜色好看的,闻起来也好闻的。」
「色香味俱全,你说了等于没说。」
我嘟囔道:「他吃了等于没吃。」
「我明白了,」朱清一点即明,「一定让他们做得好看。」
药我还是日日让人煎,可是我再也没见到尹亭挑剔饭菜的味道,眼见着还是那样。
我有时会上街买糖葫芦,依旧给尹亭一串。他倒也吃,大抵是不觉得酸的缘故,吃得总比我快。
吃完了就坐在院里的摇椅上吹风,一人一张,能躺上一整日。
人都躺懒了。毕竟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尹亭碰过公事了。
我伸手过去,拍拍尹亭:「要不你别走了,留在这里挺好的。」
「为什么是我,不是我们?」尹亭斜睨过来,「你又要把自己剔出去是不是?」
「因为我本就乐意待在这,」我对尹亭笑笑,「所以不就只有你吗?」
尹亭默了默,神色无澜
「我还想说,」我挠了挠尹亭的手背,轻声说,「我觉得小蛇也挺好的,跟你一样……挺好的。其实只要不在皇宫里,什么样都是好的。」
大抵是被风吹懵了,我竟然在劝尹亭放弃他长久以来筑下的根基,以及生来就有的家世和荣华。
可我心里明白,成不了的。
「好。」尹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