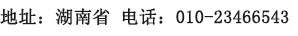我心目中的年,从腊八就开始了。中午的腊八粥混合了羊肉跟各种豆子,每人一碗。
“妈,为啥不每天吃腊八粥呢?”豆子混合的香味层出不穷,平常豆子是炒来吃,粥里也没有羊肉。
“谁天天过腊八?以前是要断粮了,把栈子里剩的所有粮食都扫在一起,最后吃顿饱饭,让人记住不能懒,要多劳动多种地多储备粮食的意思。”妈每年都这么解释。
“谁要断粮了?让谁记住?断粮了还有羊肉吃?!”哥扛着个大碗,很不服气。
“吃腊八粥还封不上你的嘴。”爹发话了。
“反正过了腊八就快要过年了。”妈解释不清楚,只好糊弄我们。
“过年了?腊八就开始过年了?”瞬间忘记了扒拉东西,过年像一颗星星忽然亮闪闪的在眼前了。
“傻,还早着呢,你不知道一个月有几天吗?”哥打击不到我,我知道要过年了,心里偷偷乐起来。
等到腊月二十几。我跟哥会被妈领着,到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王裁缝家量尺寸做新衣服。
各色花布摊在炕上,裁缝的大桌子上,被剪刀剪过的各种布条五彩缤纷,都崭新崭新的,散发着商店的味道。在王裁缝宽大温热干燥的手掌下,我兴奋的红了脸,憋着笑,眼睛开心的眯了起来。
量完衣服,觉得自己是一个新的人了,晚上跟巷子里孩子捉迷藏跑得飞快。哥也像变了个人似的,特别和善。我知道哥也在想新衣服,于是觉得我们两个是很特别的孩子,这天的捉迷藏就玩到特别晚。
过年一步一步拉开了序幕。
大牛家开始杀猪了,我们都跑去看,一群孩子挨挨挤挤挡住了大牛家的大门。
“去耍去,吃肉还早着呢。”杀猪的张屠户穿着一件冻得有点硬的黑胶皮围裙像个将军。张屠夫的围裙上一股血腥气,露出来的半截胳膊毛发丛生,鼻子旁边一颗疣子突兀而恐怖,盯着他那颗疣子,只看到他上下翻飞的嘴唇跟嘴角的一点唾沫,恶心而残忍。孩子们哄一声跑远去,好像他不单会杀猪,还会杀人一般。
“他身上带着杀气。”妈总这样说。
果然他走过来就提着一把刀,我们不知道他的刀是从哪拿的,看着明晃晃很长一根刀在阳光下刺眼地亮着,就觉得呼吸紧张起来。
一群人拥着张屠户,带着绳子棍棒往后院去了。我站在那里,设想着他们怎么对付那只肥头大耳的猪,抓?打?捆?赶?我设想着猪的惊恐跟迷茫,它知道自己今天会死吗?忽然一声长嚎从大牛家院子里传了出来。
“抓住了抓住了。”簇拥的孩子兴奋着,有人迈开小碎步鬼鬼祟祟的溜了出来。
猪的嚎叫时长时短,瞬间爆发的厉嚎声让我胆战心惊。我把手指头严严实实地塞进耳朵里,盯着他们家后院方向。
没多久,死了的猪被拉了出来,几个大人互相交谈着他们光荣的杀猪过程。
下水,除毛,破膛……
一群孩子围着看,每年春节,每家杀猪大家都要围了看,好像哪一次不一样似的。
“喂得好,三指厚的膘。”大人评论着。
看着大牛的妈切下一块脖子上的肉进了屋子,我们知道,他们要烧红烧肉。今天帮忙的人,村里几个老人待会都会围坐在他家吃红烧肉了。口水一口一口地分泌出来,又被一口一口悄悄地咽回去。
照例,大牛家会切下一排排的肋骨,分送到邻居亲戚家,哪些是去年,前年,或者大前年送过肉给他家的,哪些是长辈必须送的,哪家今年没有养猪,不可能杀猪的,都会一一想到。
我们永远无法判定自己家算不算被送的范围,第一家杀猪的人家成了我们羡慕的对象。
我们跟着大牛,看他被妈安排把肉送往哪家,如果恰好进了自己家院子,当然这家的孩子就不会再跟着出来了,其他的孩子假装着游戏,跟着大牛回家,然后往下一家去。当然,大牛也显得特别庄重,不跟平常的同学朋友打招呼。想吃肉的秘密隐藏在所有孩子心不在焉的游戏里。
杀了的猪,一半卖,另外一半除了分送几家,其他的分门别类。内脏一般归屠户,等于工钱;脊背上的肉切一部分红烧肉块,切一部分肉片,根据烧白或者糖醋肉片的要求切成不同尺寸;腿子肉切丁,准备平常作臊子面;油熬了,大块的猪油冻结起来,这一年都有猪油吃了;油渣剁碎了,包饺子格外香;其他肉基本上全部切丁,烧柴火,大锅全部炒了,加很多盐巴,等凉下来连肉带油一起装进一个大坛子里。咸肉可以吃半年,一直吃到收麦。所有的骨头剔下来,春节炖了吃。猪脑袋放在年三十晚上,跟蹄子尾巴一起炖,那是要文火大锅炖一夜的,连夜里的梦都是香的。炖好的猪头肉拆下来,当妈的拆了肉每个孩子给一根大骨头抱着啃,肉烂自香,骨头上的肉比炒的肉好吃,那个滋味是过年才有的滋味,平常偶尔吃肉,也没有人会傻到买带骨头的肉。炖猪头肉的汤自然成了皮冻,调了葱姜蒜醋,谁想吃自己去吃,破天荒的没限量。
落在男孩子手里的,是猪的膀胱,被吹了起来当足球踢。饿急了的乌鸦成群蹲在光秃秃的树上,耐心地等待着,稍微不留神,孩子珍贵的玩具就被乌鸦抢走了。
家里杀了猪,孩子唯一能掌控的就是那两根猪腰子,用柴棍穿了,晚上烧完炕,丢进柴灰里烤着,等猪腰子的主人都耍的忘记了时,细心的妈往往会招呼。
“炕洞里还有东西哦。”
孩子就一窝蜂的下了地,抢着用叉棍扒出来,在地上拍打着灰尘,拣起来倒腾着两只手让它变凉。果然已经烤得外焦里嫩,散发出烧烤肉类独有的香味。本来已经吃饱了肉的孩子,还是口水滴答,等不得彻底凉下来就伸手去你撕一块我撕一块“唏溜唏溜”的一边吹着一边嚼起来。
“给我一块。”妈也忍不住了。一家大人孩子都吃得开心。
“我就不信红烧肉比它好吃?”唯独当爹的一脸鄙视。孩子看着爹笑,没有人接他的话茬。
大牛家杀了猪,我家开始磨豆腐。
磨豆腐一定放在半夜,到磨坊里去。我打着盹,守着,舍不得睡觉,透过水汽看到大人推磨,驴一样一圈一圈地推。碾米磨面都有机器,只有磨豆腐要用手推的碾子。
我等啊等的,困得看不清人形了,被磨坊邻居黄毛家拉去,磕磕绊绊的就跟着去了。
进了黄毛家屋子里,也是一屋子人影,在煤油灯下晃来晃去的热闹。
“过来,有好吃的。”黄毛的妈一把将我拉到炕沿,递给我一个碗,碗里的肉香瞬间熏醒了我。暗红的,纹理细腻的肉糜,捣碎了加盐加蒜泥,口水差点顺着因为瞌睡而松弛的嘴巴里漏出来。我抓过筷子就着碗沿扒了一大口,鲜香无比。
“好吃吧,狗肉。”一大家人都在那笑,吃得热闹而隐蔽。黄毛靠过来,跟我两个背对着炕沿并排站了吃,他对着我笑,笑得很得意。我觉得今天的黄毛不是平常的黄毛,再不敢揪他的头发,只担心他想起来这件事情,低了头尽量加快吃肉的速度。
我想到了他们家那只黄狗,它怎么就死了呢?一边琢磨着它是怎么死的,一边吞食着它的肉,一边想怎么我们家不知道养条狗呢?又不需要找草喂,又不需要放牧,死了也有肉吃,多好。
吃完肉又被送回磨坊,磨坊中的水汽越发升腾起来,一些人在大锅前忙乎,我找不到妈,肚子暖和了,整个人都迷糊起来,就睡了过去。
等我第二天醒过来,家里到处都是豆腐的香味,我自己也在家里,看着衬了纱布的大筐里变戏法一样的两大筐豆腐,才确信昨夜家里真的是磨了豆腐的。
豆腐已经被妈切成大大小小的块,手摸上去居然还是温热的。
“给,吃了快点去放羊。”妈把一大块豆腐递给我,守候了一夜的豆腐终于嚼进了嘴巴,年的特别处就是啥都多,连豆腐也多到可以随便吃了。
“这么多豆腐怎么吃得完?”
“要送给邻居亲戚家一大部分,余下的煎了,冻了留着吃。你哥早都已经送了好几趟了。”果然看到有一筐豆腐已经只剩了一半,看来我家磨豆腐,一个队里的人都不用磨了。
“昨晚上我做梦还吃了狗肉的。”
“做梦吃的?哪有这么好的梦?我也去做一个。”妈笑了起来,莫非我是真的吃了狗肉的?我有些微的失望,总觉得那只是一场梦,虽然吃起来很香,却无法确定那些肉是不是真的进了肚子。就像梦里的面包,雪糕,苹果……
越到年前,越忙,越兴奋,也越热闹,家家户户都忙到翻天覆地。扫尘,洗被子,絮棉絮,缝被子,屋里屋外焕然一新。和面,烤饼子,使油锅炸油饼果子麻花散子。每年这个时候,也恰好是孩子们学习和面翻花做各种花样小吃的时候。
“明彩,烧点花椒水和散子面。”哦,原来散子的小泡泡是花椒水的功劳。
“这样切,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拿起来,翻。”我看着妈手上翻出来的漂亮麻花。大大的面板上放满了我们的杰作,妈还鼓励我跟哥把面团弄成各种花色,甚至可以做成小猫小狗的样子,一一放入油锅。看着自己做好的东西在油锅里上下翻腾,立刻觉得自己也是大人了。
“他爹,把那些葫芦切碎烤葫芦面饼子。”妈忙着安排,于是爹把煮熟的葫芦切成小小的块。妈忙完了别的,开始捣葫芦,撑个大勺子,用勺子背用力压下去,碎葫芦就四周挤了出去,妈捣了半天,叹气埋怨。
“切的太小了,不好捣碎。”
“就没法跟你干活,啥事都挤兑人。”爹扔了手里的家什,掉头去炕上躺着生了气。妈扑哧笑了出来。
“我说的是真话,怎么又成挤兑你了?”
“你嫌我切大了就直说。”
“真的是切小了不好捣碎,切大一点才方便。”妈一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解释,干脆把大勺扔了。“笑得人力气都没了,真是的。”
爹半信半疑的爬起来看看,试着拿勺子去捣葫芦,估计这次的勤快用错了地方,也就不再生气。
大年三十赶着把新衣服拿回来,妈快快的订上扣子,压在枕头下,等待明早穿。一家人忙着,打扫院子,挑水,把大年初一的饺子包好。初一不得上井台,不得扫地扫院子,不得用菜刀,有一堆的不能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睡着吃。一年忙到头,这是最幸福的一天。看着天暗下来了,我跟哥抢着贴对联烧纸放鞭炮。
初一一大早穿了新衣服,整个村子的孩子都开心起来,呼朋唤友的上鸣沙街去,大的带着小的,成群结队走路去。鸣沙街过年天天像赶集,有冰柿子,有葵花子,有花生,有水果糖。口袋里几角一元的压岁钱派上了用场。做父母的辛苦了很久,也没了上街的兴致,关了门在屋子里睡懒觉,睡饿了起来有熟肉有饼子有饺子有烩菜,热一下吃了继续睡,好像一年辛苦的瞌睡都要在这一天补回来。
惠宁的大爷爷已经老到弯腰驼背,据说年轻的时候迷恋鸦片,被强制戒烟。
“那时候啥戒不掉?命都戒得掉。”爹说起这些事情总是神采飞扬。
“喊得一个村子都听得到。”妈补充着。
“直接捆着,只给点水喝,民兵看管着,七天就戒了。”
这个戒了鸦片的老人,一年四处晃荡着,妈说新社会也没有改掉他的旧毛病,还是想方设法的去赌博,种地这种事情没有沾过手。
过年过节的时候,村子里的老人到哪一家串门,都是好吃好喝招待,加上家家储备丰盛,人也变得格外大方起来。惠宁的大爷爷每年这时候就从外地游荡了回来,没有人计较他农忙的时候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回来帮忙照看一下孩子以及院子里的猪羊?他成了家家的座上客。
“大爷爷,大爷爷,我给你拜年了。”惠宁跪在炕上,冲着坐那抽烟的大爷爷磕头,屁股撅得老高。
大爷爷稍微偏了偏身子,装听不到看不到。
“大爷爷,大爷爷,给压岁钱。”惠宁又磕头。
“你大爷爷的钱都长在肋骨上的,哪能撕下来给你?”惠宁妈站在地上看热闹。
“大爷爷大爷爷,我给你倒糖水喝。”惠宁果然爬下炕去倒了杯开水,抓了一大把白糖放进去,又拿根筷子搅了搅,伸着舌头舔了舔。“啊,真甜啊。”忍不住边走边喝了一大口,端了过来,先把杯子放炕上,开始往炕上爬。
大爷爷伸手把杯子端起来,一边暖着手,一边很大声的喝了一口,嗓子咕噜咕噜的冒出一串声音,舒服的叹了口气,咂咂嘴。
“看把你能的,从你大爷爷身上拿到个压岁钱。”惠宁妈嗑着瓜子,笑了起来。
“看把你能的。看把你能的。”炕上的淑宁推了一把惠宁,跟着她妈笑起来。惠宁又被推的掉下了炕,并不计较别人在做什么,依然认真的爬上来。
“大爷爷,大爷爷,糖水甜不甜?”
大爷爷呼哧一声吸了下鼻子,又端起杯子来喝一大口糖开水,满足的嘘气。
大爷爷的沉默让炕上的亲戚跟邻居家来玩的孩子都笑了起来,本来闲话的人集体开始注意惠宁跟大爷爷的较量。
“这个丫头硬气,今天一定要从她大爷爷那搞出点东西来。”邻居家的婶子也笑着。
所有人看着装聋作哑的大爷爷,也看惠宁还有什么招式。大爷爷吸了两下鼻子,忽然从鼻腔溜出两串鼻涕来,惠宁眼疾手快,伸出一只小手接了上去,一滩鼻涕恰恰好落在了惠宁的手上。一群人忙着拿帕子给惠宁擦手,边笑边骂。庆幸没有把鼻涕落在床单上。惠宁傻在那里,撇了嘴要哭出来的样子。
大爷爷手伸进口袋摸了起来。
“你大爷爷给你掏压岁钱呢。”惠宁妈笑着拽了惠宁的手一边擦一边安慰她。
惠宁期待地看着大爷爷,忘记自己手上的恶心。果然,大爷爷摸了半天,给了惠宁一个两分的硬币。惠宁高兴了起来。
“惠宁给大爷爷接了把鼻涕,得了两分钱的压岁钱。”淑宁总结了一句,一屋子的人都哄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
“这还是过年了,要换平常接两把鼻涕也得不到你大爷爷一分钱。”
一把鼻涕两分钱的故事立刻被我们知晓了,一个巷子的小孩子都追着惠宁喊“一把鼻涕两分钱。”惠宁甩着两只松散的辫子,雄赳赳气昂昂的走着,“我要买水果糖,两分钱也能买十颗,馋死你。横!”
大年初三一大早就得放火炮,谁家的火炮响得早,说明谁家的人勤快。
“他爹,起来放炮了。”妈总是会在半夜醒来。
“放个屁,爹们一年都勤快得很,非要今天装勤快?要放自己放,三更半夜的疯了。”爹卷了被子继续打鼾。妈挪过半炕,把炕这头的哥拽起来。
“我要睡觉啊,不弄我。”鸡才叫头遍,正是睡得最踏实的时候。
“乖,你放了炮明天随便睡到啥时候,我不喊你。”
哥被妈骚扰得没办法继续睡,只好起来去放响三个火炮,一家人继续沉入睡乡。哪家天亮了火炮声才响起,就被邻居家偷偷耻笑。
“初一的粉汤,初五的饺子,初七的长面。”妈每年过年都要念叨。
初七扯魂,怕魂魄跟着年三十迎回来的过世先人一起走了,于是家家户户开始吃长面。平常不上灶的男人洗手挽胳膊的开始揉面,擀面。
宋五姨妈正在把蒿子面跟面粉掺杂在一起,凉开水里加点小苏打,一边倒水拌匀一边琢磨别的。一年前出嫁的大女儿初二未回娘家,她心里就有点七上八下的,初三,初四,今天都初七了,还不见女儿的面。
“你来和,我大门外看看去。”宋五姨妈把面盆给宋五姨爹。
“看啥看,天天大门外头看,要回来自然会回来。”矮瘦的宋五姨爹嘴巴这样说,却接过了面盆。宋五姨爹粗活没力气,细活不会,好在当初混了个初中毕业,在鸣沙镇一家银行做事,好歹有那点工资,保证了他在家还敢大声说话。
“让你和你就和,管得我呢。”宋五姨妈虽然也瘦弱,干不了啥活,嗓门却很大。
“回家去,羊都饿了,也没人照看。你二姐呢?”看着大门外满街的孩子跑来跑去,没有大女儿回来的迹象,宋五姨妈顺手把吊着鼻涕的二儿,三儿拽回了家。
“二姐跟她对象上街了,她都能上街我们也要去。”老二挣扎着,一脸的愤怒。
“瞎说,啥对象?哪来的对象?媒人都没有,算啥对象?”宋五姨妈急了,不知道怎么下手教育一下这个跟自己一样高,比自己壮,力气比自己大的儿子,只好扯着他往屋子里走,倒像是被儿子扯着,重心都落在了儿子那边。三儿看妈只跟哥哥较劲,悄悄的从后院溜出去,翻了后墙又溜到马路上去了。
长面要和得特别硬,宋五姨爹遵循着这个原则,尽量少加水,勉强把一疙瘩面揉在了一起,中间一道缝隙怎么也折腾不到一起去,只好将就着费力的擀,憋得满脸通红。看到老婆进来,把擀面杖递给老婆,示意两个人换着来。
“你擀面,我弄臊子。”宋五姨妈把各种蔬菜切丁,看看切的手软,干脆把肉免了,就吃素面了。刚捅开的炉子,火势并不旺,热锅,下油,萝卜丁土豆丁豆腐丁番茄浆炒了半天,锅里不温不火的闷了半锅。本来切好的芹菜准备拿醋烹了做酸汤,看到这架势也偷偷的放弃了,一切做到偷工减料。
“面晾起了。”宋五姨爹总算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立刻脱鞋上了炕,等着香喷喷的长面吃。
“擀厚了。”宋五姨妈举起挂在扁担上的面左看右看,发现擀开的面并不能透过光,忍不住埋怨,扯过来放面板上继续擀。面倒是薄了,先前和不到一块的那个缝隙彻底裂开了,一张好好的面被她擀成了两张。因为心里记挂着大女儿,宋五姨妈也懒得计较,将就把面晾起来,准备稍微硬一点的时候切。
日光已经照到了炕上,宋五姨妈架不住肚子饿,三儿子跟二儿子都守在屋子里等饭吃,干脆烧水下面。
长面本身需要擀得薄切得细,并且不能断刀,宋五姨妈本来手艺一般,加上心里有事,一顿长面吃得凑合,看着要刷锅了,二女儿回来了。
“一大早晃哪去了?自己去下面。”宋五姨妈责问的有口无心。等二女儿一声不吭的去下面了,宋五姨妈出门串门去了,二儿三儿跟着溜了出去。邻居家的孩子过来喊二女儿去打扑克,于是家里只剩下了宋五姨爹。
宋五姨爹百无聊赖的待在炕上,眯了眼,渐渐的准备睡过去。
门忽然被推开,一个脸上挂伤,身体明显不灵便的年轻女人悄悄的进了门。宋五姨爹费力睁眼,发现是大女儿回来了。
“红霞,回来了?你妈念叨了好几天了,咋今天才回来?小宝呢?”宋五姨爹望向女儿的背后,等着女婿跟外孙进来,门被女儿关上了,她是一个人回来的。
“小宝跟孩子没一起?你看你大过年的,咋回来的?”宋五姨爹知道自己笨拙的女儿不会骑自行车,女婿没有回来,她莫非是走回来的?女婿家离这里还远,多半是费钱坐车到镇上,再走回来的。“冷不冷?上炕上暖着。”宋五姨爹给女儿拉了一床被子,接过女儿抱着的大包袱。
“你抱这么大个包袱干啥?”宋五姨爹发现一直是自己说话,女儿从进门到现在没有出声,也没有往前走半步。“你咋了?”
红霞挪到炕边来,一抬腿坐在了炕沿上,也不说话,侧身对着自己的爹。
“那狗日的又动手了?”宋五姨爹明白,女儿肯定又被打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不回去了。”红霞嘟囔了这么一句,侧身倒在了炕上,面对着墙躺了下去。
“大过年的,到底是咋了?”宋五姨爹急得上蹿下跳,女儿却并不理她,躺下就没有动。
等下午宋五姨妈回来,发现大女儿遍体鳞伤,忍不住一边查看一边哭,一边大声咒骂女婿一家不得好死。等大儿子喝酒回来后,追着骂骂咧咧医院看病,医院女儿就开始发烧,医院住起院来。
红霞被男人打住院的事情,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了,妈买了水果罐头,白糖等,医院里看她。
才结婚几年,我已经不大认得她了,尤其看到当初跟我们一样的孩子,现在像个成年女人一样的说话,没有自尊的躺着,比站着的人矮了一截,接受着所有来探望者的俯视,我觉得特别尴尬,偷偷溜出去等着妈,却又极想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
几天后,红霞的男人来接媳妇回家,被三爹碰个正着。
“宋五棉得像个娘们。”三爹在父母面前谈到这件事情哭笑不得,“我一进院子,看到宋五跟他女婿两个人扯着个包袱,就那么站在院子里,你扯过来,我扯过去,一句话不说。我问这是干啥呢,宋五女婿说他来接媳妇回去,我呵斥他住手,好好收拾了他一顿,喊他滚,等他们家想清楚了带着没教好他的爹妈来赔礼道歉。医院了,你说宋五连个屁都不放。”
“听说耳朵聋了,上次打了就半聋了,医院发烧就彻底聋了。”爹补充着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新闻。所有在场的人都愣了,明显没想到情况这样严重,为自己先前看热闹的心态感觉丢人。
“他这是犯法的。”哥忽然插了一句。“应该去法院告他们。”
“人家自己家的事情,人家不告,我们旁人能说啥?”爹意外的没有对哥的无礼给予责怪。
“关键是告了,就算赢了,离婚吗?离婚了咋办?她爹妈养活她?她又不能吃苦,长得又不好,现在残了,更没有人要了,何况儿子丢那家她舍得不?”
所有人都闷闷的坐着,没人再发言,只好在年的味道里继续沉默。
“算了,不干涉人家的事情了,今天二十三,晚上要燎干了,我早点回去抽两梱麦秸来堆着。”
“对了对了,今天要燎干。”我跟哥都兴奋了起来,妈也起身去准备了。
“正月二十三,大人娃娃燎个干。”从下午开始,巷子里的孩子就兴奋的重复叫嚷着这句话。这是一年中唯一一次大人跟孩子玩一样的东西,也是过年的最后一件大事,过了今天,年就算过完了。
“玉皇大帝想要惩罚人间的老百姓,王母娘娘善心大发,想了个招来保护老百姓,就跟玉皇大帝说,正月二十三那天,人间将有一场灾难,所有的人都要在火堆里烧死,就不劳烦你动手了。要不,你那天去看看?王母娘娘派人先到人间通知,要大家在正月二十三这天,到处放火,火里撒上盐巴,并且每个人都要从火堆上跳过去,可以免灾。到了这一天,玉皇大帝带着一大堆神仙,从天上往下看,果然看到处处是火堆,人在火堆上着急的跳来跳去,烧得噼里啪啦的响。就这样,玉皇大帝被蒙蔽了过去。为了纪念王母娘娘的善心,每年的正月二十三这一日,都要燎干。”妈给我讲燎干的来头,我等不及妈讲完,就着急的想到巷子里去看看。
十字路口已经堆了很大几梱麦秸,大牛的爸爸,三爹,爹,张大,张二,……很多大人都在那里,一边说话一边等天黑,孩子们兴奋地跑回家去又跑出来,跟妈说一声快开始了,又出来看开始没有。
等天黑透了,大人慢悠悠地把麦秸点起来,撒了大把的盐巴在麦秸上,很快就噼啪啪的烧了起来。年龄大点的男孩子开始不管不顾地跳起来。看着一个个人影子从火里冲出来,所有人都兴奋了,大姑娘小媳妇也不再矜持,依次的从火堆上往过跳。年龄小的孩子急得伸一条腿往火里跨,当爹的自然知道孩子的心情,因为自己也是急迫的,于是借了抱孩子跳,也跳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孩子抱的,甚至拄着锹把,很神气的跳过去。当然,年龄太大的,只好把两条腿依次的从火堆里跨一下,就退到旁边看热闹了。
等所有的人基本都跳过一遍了,加柴,加盐,火堆成了孩子的天堂。着急的孩子也顾不得顺序,有些从这边跳,有些从那边跳,刚好在火里撞个满怀,同时跌入火堆。手脚快的自己爬起来跑了,在火里挣扎的,被边上的大人一把扯了出来,别的到也没有损失,往往头发眉毛被烧得半秃,会持续被伙伴嘲笑很久。
妈特意放一些小块的黑面饼子在我的口袋里,悄悄叮嘱跳火堆的时候,要让黑面饼子掉进火里,代表穷日子过去了,来年都只吃白面饼子了。掉进去是个难度有点大的事情,代表我必须用力跳,口袋还得比较松,饼子能跳动,至少我不能拿在手里,跳的时候丢进去。我尝试把饼子塞进裤子兜里,那是个很浅的装饰口袋,一次,两次,三次,每次从火堆里钻出来,我都摸得到它鼓鼓的还在。这个任务成了负担。哥看到新加的麦秸燃起来,火势太大,叮嘱我不要跳,他自己却飞奔而过。等哥跳过去,我缠着他要一起跳,哥被我缠得没法,拉着我一起跳,他快我慢,跨过火堆后就摔了一跤。我飞快的爬起来,在旁人的哄笑声中溜入黑暗,忽然想起什么,再摸摸口袋,黑面饼子没有了。我像完成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心情放松下来。我一直想问妈,为什么每年都丢黑面饼子,第二年还是要吃黑面饼子?以至于我每年都要想方设法假装让这块饼子自己不小心掉进了火堆里。
等大家都跳够了,堆积起来的麦秸也烧完了,扬场的高手上场,开始用木掀扬起星星点点一闪一闪红色的麦秸灰烬。一锹上天,拉出一大条红色的弧线,在天空中撒开,大家一起叫。
“麦子花。”“今年麦子要丰收,好红火的花哦。”专门有人在旁边说些吉祥话。
“玉米花。”第二锹上天。
“今年玉米大丰收哦,花又红又密。”
水稻花,豌豆花,苹果花,大麦花,糜子花…….我们能种植的农作物挨个的要被喊上一遍,并且样样丰收,围观的人喊一声跟着欢呼一次,好像丰收的年成就在眼前。
等所有的花都扬完,燎干人员集体冲进早已经铺散开闪着火星的麦秸灰烬中,飞快跺脚踩了起来。留下一个红点,就等于多了只破坏粮食的老鼠。一大堆鞋子踩地的声音踢踏做响,很快老鼠就被消灭完了。
大人,老人,小一点的孩子回家睡觉,中等大小的孩子正精力旺盛无处发泄,顺便要看看几个巷子外同龄的异性,自然成群结队的挨个火堆去串,这家收场了赶下一家,有时候甚至赶到黄营去,尽兴而归,连梦里都是挤挤挨挨跳火堆的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