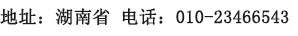个人认为,打游戏是某个阶段发的瘾,玩过那一阵儿,就不治自愈。我在二十多岁曾是“打坦克”的通关高手,后来打“立四麻将”也升到相当高的级别。但是某一日,忽然心灰意冷脖子疼,此生就潇洒地告别了游戏。但若妄说所有人都如此,我的老爸即刻就打了他儿子的脸,八十高龄的他老人家孜孜不倦地在电脑上打“接龙”,打了十几年,仍然兴致勃勃。
仿佛在一夜之间,游戏就侵略了中国人的大脑,我们当下就把“玩物丧志”之类的古董教条原封不动地还给老祖先了。在大学里,有的学生甚至把功课当成了副业,游戏打累了,调剂一下,去教室听会课休息休息,顺便混个出勤。这事后来激怒了一向温和的《人民日报》,遂发文嘶吼: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
但不可否认的是,游戏还是扑面而来了。 的数据显示,全球游戏产业规模已经突破千亿美元。而玩心最重的还是中国人,年中国的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亿元,稳居世界老大的交椅。
关于游戏,本来是生活的一个开心调剂,只要不沉迷,就行!呵!自己写出来都觉得这是一句多么幼稚可笑的屁话。游戏开发商绞尽脑汁就是想让人沉迷不拔的,大多数人的自制力在游戏面前都弱不禁风。尽管说什么都没用,但还是要心虚地说一句:正常的游戏可以有所克制地玩,那种诱导人犯罪或 之类的邪恶游戏如“蓝鲸死亡游戏”之类还是要像对待毒品一样,丝毫不能沾染的。
那是高压线,谁碰谁就灰飞烟灭。设计这种游戏的人,如果说他们还不是赤裸裸的魔鬼,那还能是什么?
似乎管得有点宽了,但是青年兴亡,家国攸关,匹夫也有责,说几句求个心安。
回头还说游戏,原以为是个现代词儿,因为印象里的古人们都是正襟危坐的,就是游戏也雅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他们“曲水流觞”,那个要命的杯子漂过来,你就得憋一首诗出来,问题是我连呆霸王薛蟠那两下子都没有,玩得这么悲哀绝望干什么?
后来查阅了一下方知,这个词不仅古代人用得很溜,而且是从不苟言笑的佛家传出来的。把“不苟言笑”和“游戏”放在一起,倒正是验证了我的无知,今天要说的“游戏”二字,恰是说明佛家才不那么死板,人家是活泼泼地。
《维摩诘经》里文殊菩萨赞叹维摩诘居士时说:“这个人不好应对呀!他‘诸佛秘藏无不得入,降伏众魔,游戏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
这里说维摩诘所拥有的“游戏神通”,就是可以自在无碍地以神通变化降伏众魔并接引世人,其智慧和方便法门都挥洒自如。
《智度论》曰:“戏名自在,如师(狮)子在鹿中自在无畏,故名为戏。”(呵!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考虑鹿的感受?)
慧远疏曰:“于神通中历涉为游,出入无碍,如戏相似,故亦名戏。”
跟“游戏神通”意义相近的是“游戏三昧”,“三昧”指“正定”,就是自在游戏而不失定意。这是相当高的境界,就像《般若经》上说:“宴坐水月道场,降伏镜里魔军,大作梦中佛事,广度如幻众生。”这是大乘佛教的 境界。意思是:所有的讲经说法无非是游戏三昧,哪里真有众生可度?真有佛法可与人呢?
《大般若经》还讲到一种游戏三昧,也备一览:师子游戏三昧也叫师子游戏等持,为三摩地的一种。当佛陀进入这种三昧之中,将使三千大千世界震动。
《景德传灯录》卷八记载唐代禅师普愿:“入中百门观,精练玄义。后扣大寂之室,顿然忘筌,得游戏三昧。”
普愿禅师得鱼忘筌,舍舟登岸,唱着歌入了大自在地,这也是历代文人们最向往的,于是他们趋之若鹜,当然成就不一。进了门,却不空手走,佛家的好东西都被文人们偷出来了,连深通佛法的王维也顺手牵羊呢。
王维在《山水诀》里说:“手亲笔砚之余,有时游戏三昧。岁月遥永,颇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如此才能“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他的意思是说,书画文章也有般若秘境,自由王国。
《孟子》有句话,“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宋代陈岩肖的《庚溪诗话》说苏东坡虽然宦途失意,命运坎壈,却能随遇而安,“时以文笔游戏三昧。”他还是一枚大吃货,“日啖荔枝三百颗”,他发明“东坡肉”、“东坡肘子”,如此则不能不说其“智亦大矣”,“智”到什么程度?“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能写出这样词句的人,才真道出自然之性,如平和清净的湖水映着高天上流动的白云,不喜不悲,不惊不动。
在苏东坡的身上,儒释道三流归一,儒家“行其所无事”、道家的“逍遥游”与此佛家的游戏三昧原是钟鸣鼓应,琴瑟和谐的。他们都不是纯粹执着于静谧和枯寂,而是主张静中有动,动静一如,在日常生活的有为中,修成无为的静定,正如无住禅师所言:“真心者,念生亦不顺生,念灭亦不依寂。……无为无相活泼泼,平常自在。”
言至此已尽,再说“游戏”,不能不提起一个高僧来,那便是济公。
说到济公就不能不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他吃了鸽子肉,却能从嘴里飞出鸽子,他喝了酒,却能吐出金子为佛像装金,他于尘世里游戏神通,“于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事”,仍是度人的菩萨行。
所以我们普通人千万别再以这半句话来为自己喝酒吃肉遮羞了,因为济公还有后半句:“世人若学我,尽皆入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