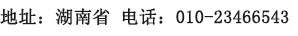我是阿月,沙溪古镇上的姑娘。是我的歌声把你引来的吗?啊,是这个叫唐佳的大理女孩,她的故事把你们引来的吧。
是的,千百年来,我一直在大理,在剑川,我一直在沙溪,我在这里等待。我看到你们来了,我的客人。来,跟着我,跟我走上寺登街的石板路,听听街边的流水,摸一摸马帮的炊烟熏黑的土墙,听我讲马帮的故事。
去沙溪的山路上,我 次听说了阿月和马锅头。那个时候,大理是富庶的南诏国,盛产茶叶和盐巴。而山那边的高原上,有一个民族,需要茶克化每日吃下的奶和牛肉,需要盐巴维持身体的力量。于是,一群群人,走上了贩运茶和盐巴的路。
马帮的领头人,驮着锅,负责马帮的生活,他就是马锅头。唐佳说,马帮就像现在的物流公司,马锅头,是物流公司的CEO。马锅头带领马队,在这里歇脚,添加草料,然后再次上路,顺着有水的地方,一路向西,到吐蕃,或是更遥远的地方。马帮走过的这一路,有辛劳,有伤病,有爱情,更有凶险。
沙溪是南诏和吐蕃两个民族之间的纽带,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马帮的必经之地。马锅头和阿月的故事,一定是在沙溪发生的——虽然那时,茶马古道上,必有许多沙溪这样的古镇。但岁月无情,故事还在流传,因交通闭塞而幸免于现代文明的淹没与侵蚀,又因瑞士人雅克?菲恩纳尔博士的发现与疾呼而被保护性开发的古镇只剩下这一个。
就是在这里,这样的深山里的小坝子,这样清幽的古集镇,女人们背来上山割的草料,与马帮交换生存必需的盐巴;男人们在城垛上守卫,他们背后的院墙上,还留存着劫匪的弹孔。
马帮有了一个难得的温柔的夜,马儿也卸下重重的背负,吃饱了鲜美的草料。兴教寺里诵了一夜的经,古戏台上唱了一夜的戏,马店里,椽子熏得更黑,墙上多落了一层烟灰。第二天,马锅头带领马帮出发了。马锅头的手腕,添了一只镯子,是阿月家传的龙凤镯子中的一只。
马帮离开了,明天又有一个马帮来。马锅头走了,明天又有另一个马锅头来。阿月开始了等待。
你问我为什么叫阿月。是唐佳告诉你们的吧,我叫阿月。她告诉你们,她叫唐佳——唐朝的唐,佳人的佳。你们都笑了:唐朝佳人。——唐朝,大理还是南诏国的唐朝。她还唱起了《小河淌水》的歌,哦,向沙溪来的车上,你们都唱起了这支歌:“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唐佳说,阿哥,是我的行走在山间、停不下脚步的马锅头。唐佳说,《小河淌水》,这是我的歌。是我对马锅头的守候。
魁星阁的古戏台上,洞经古乐、白族传统的霸王鞭仍在喧腾。兴教寺里已没有香火,六百年的雕梁画栋,经历过战火,经历过地震,还经历过我们想不到的劫难吧,静静地立着,看淡了 的风月。我看到一副牌匾,记住了李元阳的两句诗:“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花人。”
石宝山石窟的馆长董增旭先生,语速很快,他的讲述是骄傲的,也是焦急的。他曾在敦煌学习多年,曾与中外学者一起研究石窟艺术,曾在国外的讲坛上与西方学者争论对南诏文化的理解。他想把南诏文化的所有遗产都讲给我们听,包括寺登街的马店,包括寺登街不远的他的石窟,包括发现沙溪、呼吁保护沙溪的雅克?菲恩纳尔博士,包括海外专家学者的捐献、支持与复建工作中对于古迹保护的严苛,也包括少数西方学者对于南诏文化的误读。
在兴教寺的那副牌匾前,董先生讲述着李元阳如何被贬,如何来到兴教寺,而被教馆的先生们忽视之后,写下的这首诗。同行的文人们,难得有世俗意义上人生得意的吧,就像此时的李元阳。文汇报副总马申先生说话带点淡淡的海味:男人到了四十五岁,要学会放松;五十岁,学会放下;五十五岁,学会放弃。他又说:人生就像嚼甘蔗,嚼一口,吐一口。有女同行悄悄耳语:那我们女人,是不是还得提前五年?
嚼一口,吐一口,毕竟有过甘甜的滋味咽下。可要放下的是什么?我的目光在寺院中搜寻,李元阳吟咏的杏花早已不在。如若在,它会在意谁人的惜与不惜?阿月,你说,有一些,你何曾拿起?有一些,又如何放下?
你又问我:你的马锅头叫什么名字。你想叫他阿鹏?我们白族的男孩,都叫阿鹏。就像女孩,都叫金花。你们看过《五朵金花》,都听过“莫是剑川花开晚,误了好时候”,都知道“剑川来的阿鹏”。
可我,只叫他马锅头。
马锅头走了,他说他会回来。他的手上,戴着我们定情的镯子。他说,他会回来。可是,我等了一年,天,没有等到马锅头。
我多想把故事停在这里,不往下继续。我还想把它写成,第天的时候,阿月等来了她的马锅头。可故事不是这样,唐佳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马锅头遇到了劫匪,绑了票。马锅头临死的时候,告诉他的副手——唐佳说,也就是“二锅头”——马锅头让“二锅头”告诉阿月,他到了外国,爱上了那里另一个美丽的女子,留下了,不走了,叫阿月嫁人吧。
“二锅头”带着马帮回来了。他见到了阿月。他说:阿月,你死了心吧,马锅头他爱上了外国的一个美丽女子,他不回来了,他让你嫁给别人。
阿月摇摇头,下唇咬出了白印:我不信。阿月说,如果真是这样,他会把我的镯子还给我,那是我们定情的信物。
“二锅头”说:好,下一次,我回来,把你的镯子带给你。
每一次回来的路,“二锅头”都嫌太长,可这一次,“二锅头”希望这条路长些再长些。“二锅头”已经找不到一个能让自己相信的理由,说他为什么没把镯子取回来。
“二锅头”只能告诉阿月:马锅头死了,死了几年了,阿月,马锅头死了。
是的,马锅头死了,马队 回来,没有见到马锅头,我就知道,马锅头死了。
你问我,阿月,可你为什么还一直在等候?
你看到天上的月亮吗?坡上的树,绿了会*。门前的花,开了会谢。可天上的月亮,夜夜陪我一起等候。
阿月要跟着马帮一起,去看她的马锅头。
马帮里,不能有女人。阿月剪去长发,换上男装,跟着马队一路向西、向南,找到了马锅头埋葬的地方。阿月加入了马帮。阿月找到杀害马锅头的仇家。阿月当上了女马锅头。
阿月给马锅头报了仇……
唐佳的故事讲完,车里一阵欷歔。我的耳边不合时宜地响起一首流行歌曲的旋律:“二十四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
阿月与马锅头的相守,有二十四小时吗?阿月的爱情,却是为二十四小时等候了长长的一生。没有回忆,不是回忆,所有的回忆就是此刻,所有的回忆都是守候。
阿月,我明白了,那些西方人,为什么会迷恋这样一个偏远的村庄,为什么要费心费力地去复原这样一个古老的村庄。他们来到这里住下,到田间地头,跟农民一起犁地、收洋芋。他们执拗地要求:房屋的复原,不能用钢筋、混凝土;居民不能迁出;这些木地板、木屋顶的房子,古代不需要消防车,现在也一定可以不需要。都市的文明,他们走得比我们更早更远。莱茵河的水,曾经比滇池还要腥臭。都市的疾病,那种焦灼急躁,那种总怕被落下的恐惧,他们体验的,也比我们更深。
他们是来疗伤的,他们是来治病的。他们是来这里,寻找美丽的乡愁。所有的外乡人,都可以将沙溪当作故乡。而沙溪,永远是沙溪人的,它不会有古镇商业化之后的躁动,不会有被外乡人“占领”之后的空洞,沙溪人的脸上,是千百年的恬淡安详。
回程的飞机上,同行的记者们说起马申先生。他曾有一个美丽的才女妻子,为给妻子治病,他卖掉虹口鲁迅故居近旁的洋房,白天忙着“买汰烧”,晚上再赶去夜班。送走妻子,他有了新的爱情,又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在我们的请求下,他拿出过手机,让我们看他的新夫人,听